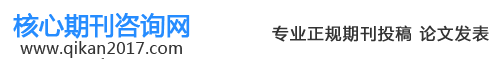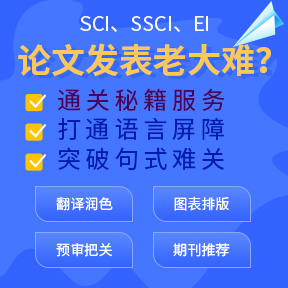乡村共治格局下的“政—族”合作
来源:核心期刊咨询网时间:2019-10-31 10:0612
摘要:摘 要:广东省蕉岭县以村民理事会运作为核心的村治实践,是当代宗族与政权在客家基层乡村治理中互动的典范,通过政权治理力量对宗族治理力量的引导与培育、宗族治理的自我转型与发展,以及在双方各自治理优势基础上的分工与协作,实现了乡村共治格局下的政族
摘 要:广东省蕉岭县以村民理事会运作为核心的村治实践,是当代宗族与政权在客家基层乡村治理中互动的典范,通过政权治理力量对宗族治理力量的引导与培育、宗族治理的自我转型与发展,以及在双方各自治理优势基础上的分工与协作,实现了乡村共治格局下的“政—族”合作。通过党政力量的适当引导,这种“政—族”合作主要是以双方在治理场域中的异质性与同质性共存为基础,通过彼此间异质性的调适与同质性的整合来实现。
关键词:共建共治共享;乡村治理;村民自治;宗族;国家—社会

《特区实践与理论》(双月刊)创刊于1986年,是由中共深圳市委党校深圳行政学院深圳社会主义学院深圳经济管理学院联合主办的专业理论刊物。
一、问题的提出
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要求“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1]。这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体现,也是新时期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深化。不少地区开展或深化了村治创新,围绕不同治理力量的共治合作形成了一批可借鉴的经验。
学界以“共建共治共享”为主题的研究主要从两个进路展开:一是侧重于对“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的理论型阐释,二是对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实践进行经验型归纳和分析。后者主要从地区个案和专业治理职能两个维度来开展,对城市社区治理的探讨占绝大多数,专业治理职能分类涉及到民政、安监、城管和旅游等方面。
共治格局要求不同的治理力量参与其中并协同合作,基于此,学界选取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治理力量为分析对象来开展研究。作为社会治理力量的代表之一的宗族在治理中的角色、功能、影响及其与国家的互动,学界已有诸多研究。吴理财认为当代宗族“在遵从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的前提下,参与村庄公共权力的角逐、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管理”[2];肖唐镖将宗族力量界定为当代乡村治理中“非正式的治理者”——与政党、政府组织这些“正式的治理者”相呼应[3];潘淑贞以历史变迁的视角展现出宗族与国家围绕乡村治理的互动及关系调适[4];徐勇根据新近的田野调查,围绕宗族在乡村的治理机制及其与国家政权的互动,提炼出“祖赋人权”[5]等概念。
相对于乡村共治格局下的治理实践推进,学界对其的认知、提炼与探讨还有待更新。以乡村治理为研究对象的成果也显著少于城市治理。有少许研究讨论了不同治理力量的角色定位与职能发挥,虽然都力图展示多力量和多主体的“共治”,但更显著地是对某个单一主体的“特写”分析。围绕“共建共治共享”中“共”这一核心特征,需从单主体分析的视角中跳出,将“国家—社会”范式引入到基层治理实践的分析中,以国家与社会各自具化的形态如政党、政府、宗族等相互间治理互动为研究焦点,进而深入地探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有效实现形式与机制,这正是本研究的出发点。本文拟阐明和回应下列问题:第一,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下,个案地区有何治理实践?第二,在乡村共治场域中,国家政权治理力量与宗族治理力量彼此发生了何种互动?第三,政权治理力量与宗族治理力量围绕乡村共治其合作的内在机理为何?
二、乡村共治:村民理事会
蕉岭县位于广东省梅州市,作为客家聚居地,在宗族象征与实体方面保持了较好形态,是典型的汉人宗族地区。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蕉岭县的宗族组织大量瓦解,但正如有学者指出“尽管宗族与宗法关系的影响在将近三十年时间中近似于消失,而实际上,他们在农村中的根基却依然存在,并以隐蔽的形式长期发挥着作用”[6]。即使在政治控制最严格的人民公社时期,虽然宗族的经济功能、治理功能和组织形式凋零,但其宗族传统和文化根基依然留存。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蕉岭县经历了明显的宗族复兴。在宗族象征与实体方面的复兴中,不仅当地社会力量被调动,海外的宗族资源也参与进来,修续族谱、修缮祠堂和“围龙屋”、大规模祭祖等宗族活动成为“家常便饭”。进入21世纪,当地围绕客家文化积极经营,同时伴随对外交流的增多,为宗族作为一支治理力量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条件。在乡村治理场域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施行以及人民公社体制的瓦解,产生了国家与乡村基层间的“权力真空”与“管理空白”,宗族治理力量借此重新“萌发”并开始了在乡村治理中的重建。从村民自治施行、税费改革再到当前村治有效实现新探索的时代变迁中,以村民理事会为焦点,宗族治理力量不断再造并与党政组织持续互动,逐渐形成了当下乡村共治的格局。
(一)村民理事会的发展历程
宗族本身具有一定的组织性,加之民間传统规约的影响,当其作为一种治理力量复兴并进入乡村治理场域时,就会呈现出一种有组织的而非散漫的特征。在蕉岭这种组织性就表现为一部分宗族最先恢复了祠堂理事会或宗族理事会,不过这种理事会并非一开始就以政治治理组织的面貌出现,而往往通过社会交流、文化民俗和经济往来等发挥功能。
1.宗族理事会的自治恢复。蕉岭县一直保持较好的宗族文化联结与族亲间交往。伴随20世纪80年代的宗族复兴,各姓宗族逐渐重建了宗族理事会来负责各自的宗族活动。随着各种宗族活动在种类和规模上的拓展,越来越多地涉及到资源分配与处置,这促使宗族理事会从纯粹的活动组织者转型为统筹宗族经济文化事务的治理者,并在与不同房支、不同族系的交往中扩充相应的内部治理与对外治理职能。这一时期宗族理事会的自我治理处于恢复或初创阶段,主动参与乡村公共治理的初衷较弱,且这一时期还有不少规模小、财力弱的宗族并没组建的理事会,遇到公共问题基本就是族中长者或个别贤达临时处置。即使是规模较大、居住集中和实力雄厚的宗族,其理事会也只是依靠民间约俗或草创的规矩来运作,是比较朴素的民众自我治理。
2.村民理事会的改造与成形。村民自治实践中出现了一种治理的“供需不均衡”,民众有着大量超出个体家户范围的公共事务需求,但行政村本身可支配资源有限,大量乡村治理事务被空置,普通村民参与乡村公益的热情低,不少村务陷入无人管或无力管的困境,村民自治的“四大民主”不同程度上被空悬。与此同时,一些宗族理事会打破行政村、村小组界限,在组织社会资源、凝聚族亲力量、推动乡村治理中却展现了显著功效。
这一情况为蕉岭县委县政府所重视,借助“全国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单位”这一政策机遇,蕉岭县委县政府设立试点开始有意识引导和改造宗族理事会,使其向更符合当代基层治理要求的村民理事会方向转变与融合。从2014年至2015年先后出台《关于培育发展村民理事会的指导意见》《农村村民理事会设立指引》等文件,在试点村与宗族长老、村落贤达共同拟定了《村民理事会章程》,为之后全面推开村民理事会实践提供参考。到2015年,蕉岭县除少数村庄外,基本实现了村民理事会的覆盖。
转载请注明来自:http://www.qikan2017.com/lunwen/zfa/14761.html
相关论文阅读
- 2022-09-17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渐进化过程的问题探究
- 2022-09-17提高高中生财政法律论文意识的思考与建议
- 2021-12-30民法典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法回应
- 2021-12-25推进河南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现实思考
- 2021-12-11网络恶意不兼容的法律构造与规制逻辑
- 2021-12-09基于思政教育的环境设计专业教学改革研究
- 2021-11-25整体性视野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论析
- 2021-11-24新形势下企业思政工作存在的问题及提升措施研究
- 2021-11-19精细化管理应用在医院档案管理中的作用分析
- 2021-11-19新时期事业单位行政管理问题及对策探析
期刊论文问答区
- 2024-04-232023年版(第十版)北大核心中文核心期刊目录的大看点
- 2024-04-18提高发表论文成功率,不妨试试这些方法
- 2024-04-02sci作者排序以投稿系统为主还是以手稿排序为主
- 2024-01-03Cell Death & Disease期刊发表论文解读
- 2024-01-032023最新期刊分区表大类21个小类254个
- 2023-12-282023年中科院期刊分区表正式发布!快来看看
- 2023-12-25圣诞元旦英文论文审稿变慢是真的吗?答案是真的
- 2023-11-162023年智能电网与能源工程EI会议推荐
- 2023-11-09SCI期刊投稿经验-各种状态解读
- 2023-11-06税务研究杂志的论文发表要求
政治法律优质期刊
- 1核心级《社会主义研究》
- 2国家级《国防》
- 3省级《成都行政学院学报》
- 4核心级《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 5核心级《中国社会科学》
- 6省级《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
- 7省级《当代检察官》
- 8省级《治理现代化研究》
- 1省级《成都行政学院学报》
- 2省级《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
- 3省级《当代检察官》
- 4省级《治理现代化研究》
- 5省级《德国研究》
- 6省级《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7省级《徐州工程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 8省级《北京青年研究》
- 1核心级《社会主义研究》
- 2核心级《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 3核心级《中国社会科学》
- 4核心级《浙江档案》
- 5核心级《党建研究》
- 6核心级《出版广角》
- 7核心级《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8核心级《哲学分析》
最新期刊更新
- 《中国政府采购》
- 《中国政府采购》
- 《农业图书情报学刊》
- 《农业技术经济》
-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 《房地产世界》
-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
- 《广州化学》
- 《物理学报》
- 《东方宝宝》
- 《新能源进展》
- 《热带农业科学》
- 《建筑经济》
- 《中国学校卫生》
精品推荐
- 12022-09-17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渐进化过程的问题探究
- 22022-09-17提高高中生财政法律论文意识的思考与建议
- 32021-12-30民法典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法回应
- 42021-12-25推进河南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现实思考
- 52021-12-11网络恶意不兼容的法律构造与规制逻辑
- 62021-12-09基于思政教育的环境设计专业教学改革研究
- 72021-11-25整体性视野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论析
- 82021-11-24新形势下企业思政工作存在的问题及提升措施研究
- 12018-10-16如何增强执法人员的法制意识提升
- 22018-03-23法学方面审稿比较快的月刊有哪些
- 32019-11-02论党内规范性文件向国家法律的转化
- 42021-12-25推进河南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现实思考
- 52021-11-24新形势下企业思政工作存在的问题及提升措施研究
- 62018-07-16基础教育阶段的思政课程定位和界定
- 72020-11-23抖音短视频对大学生思政工作的影响
- 82021-11-25整体性视野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论析
- 12024-05-154本生物医学领域的期刊,有SCIE也有ESCI
- 22024-05-15ssci收录经济学领域高分期刊Oeconomia Copernicana
- 32024-04-28录用率高、检索稳定计算机科学类SSCI期刊推荐:Systems
- 42024-04-23Sensors主办第十一届传感器与应用国际电子会议 (ECSA-11) 开放征稿中
- 52024-04-232023年版(第十版)北大核心中文核心期刊目录的大看点
- 62024-04-18提高发表论文成功率,不妨试试这些方法
- 72024-04-11AHCI哲学类期刊VERIFICHE
- 82024-04-02sci作者排序以投稿系统为主还是以手稿排序为主
- 12021-05-24刊号字母G、G0、G1、G2、G3、G4、G8是什么意思
- 22021-05-06论文引用率不能超过多少
- 32018-09-11语法翻译法的运用以及优缺点分析
- 42020-03-08发表在期刊上的论文一般多少字
- 52020-09-21疾控中心工作怎么评职称
- 62020-01-03新北大核心什么时候更新,几年更新一次
- 72020-03-08通讯作者和二作哪个含金量比较高
- 82021-02-23发表的期刊论文见刊的时候可以在知网查到吗